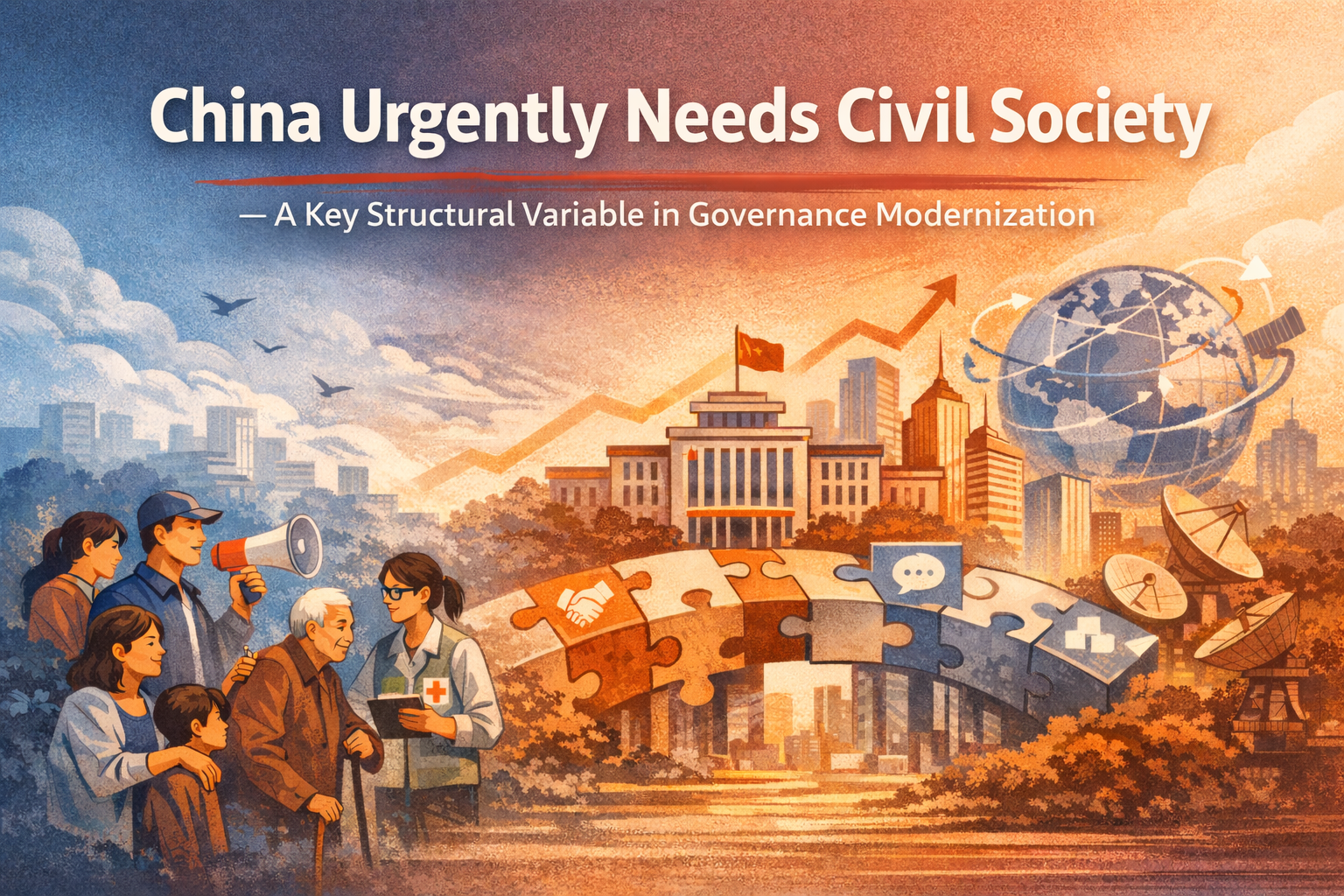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系统阐述了其制度理论。他们将制度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1.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
这类制度鼓励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参与,保障产权,维护法治,促进教育和创新。它们建立了一种可预期、可参与的秩序,推动社会成员将自身命运与集体进步绑在一起。换言之,包容性制度激发的是“全社会的创造力”。
2.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相对而言,掠夺性制度排斥大多数人的参与,将财富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产权和契约不受保障,经济活动受制于权力结构。这种制度不是为了激励,而是为了控制;不是为了进步,而是为了维稳。
这两种制度类型,在朝鲜与韩国的分化进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韩国采纳了市场制度与民主政治,实现了从战后废墟到全球科技强国的跃升,而朝鲜固守中央计划与权力集中,使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封闭与社会停滞。
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再生产机制
制度是一种自我复制的秩序结构。一旦形成掠夺性制度,它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反过来会阻止制度改革,维护现状。这种“制度锁定”机制正是许多国家在表面开放背后仍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
在《殖民起源与经济发展》(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一文中,三位学者通过历史自然实验进一步证明:在死亡率高、殖民者不愿久居的地区,殖民者通常建立压榨性制度,而这些制度在殖民结束后继续存在,成为国家发展的阻力。反之,在死亡率低、殖民者愿意定居的地区,殖民者更可能建立可持续的包容性制度。这种制度起点的差异,在数百年后仍决定着发展轨迹的分化。
繁荣的可能:制度变革的路径
三位学者认为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要同时具备如两个条件:
一是“临界点”出现,譬如遭遇制度危机或外部冲击,从而打破原有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二是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盟,特别是中下阶层与进步力量联合,推动体制变革。
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南非废除种族隔离等,都是制度突变与社会重构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