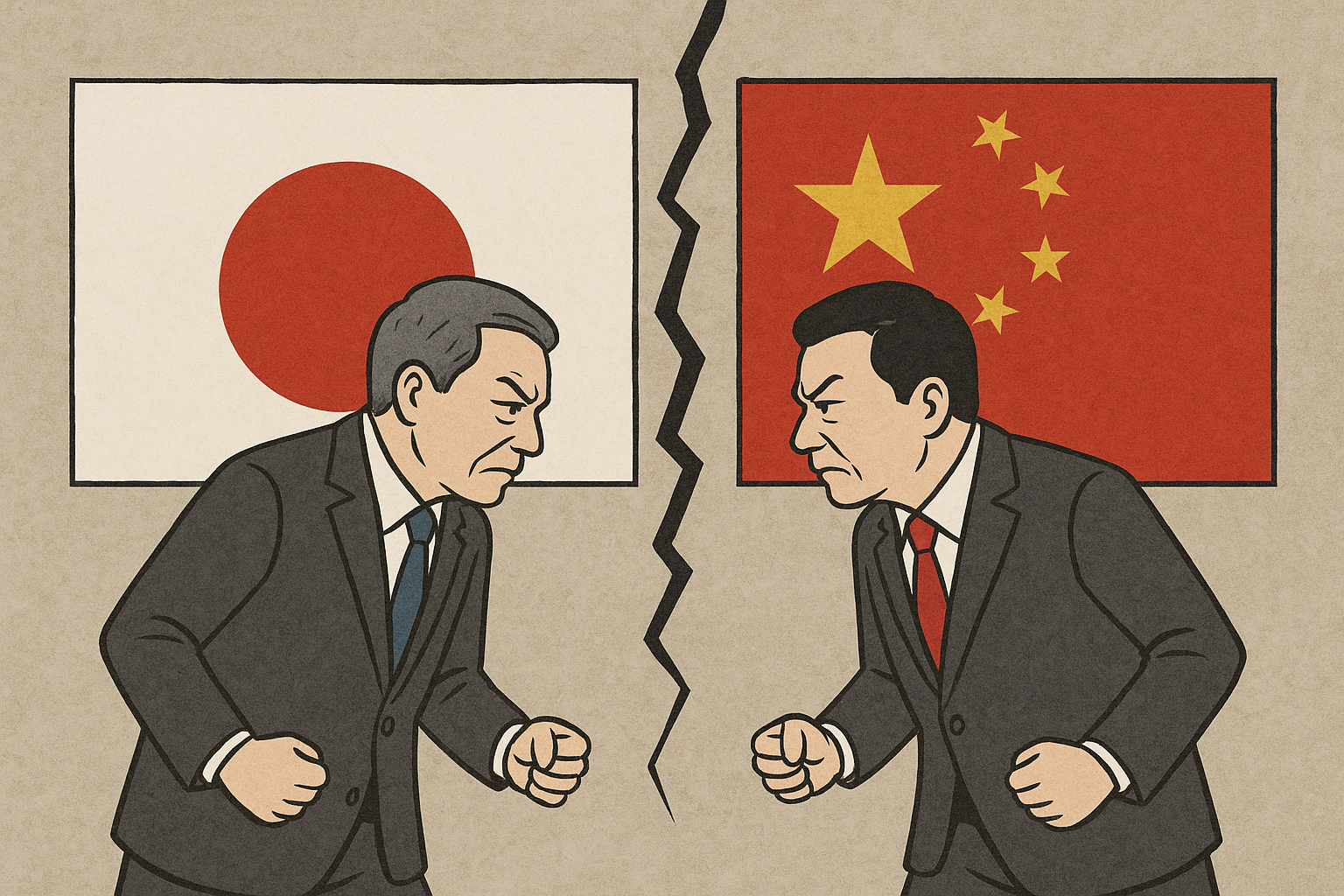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尽管经贸摩擦增多,但中日经济关系仍具有显著韧性。日本企业的中国布局虽然趋于谨慎,却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市场依然是其全球战略的关键部分。两国之间的技术、供应链与资本流动呈现“分区制”特征:敏感领域趋于分离,非敏感领域保持合作,高度成熟的制造链在区域内部重组。
未来的经济关系可能呈现三种趋势:
第一,关键技术合作减少。半导体设备、精密制造材料等领域将继续受到制度限制,这是战略性竞争的焦点。
第二,制造链合作仍然稳定。汽车、化工、消费电子等行业在短期内缺乏替代方案,依赖关系仍然强固。
第三,区域经济规则之争上升。CPTPP、IPEF等机制将成为影响双边经济关系的外溢舞台。
这意味着,中日经济关系不会因政治紧张而断裂,但会进入“竞争与合作并行”的长周期。
四、外部变量将决定紧张关系的“天花板”与“地板”
在所有变量中,美中关系是最关键的外部因素。如果美中竞争保持可管理,中日关系的紧张将被锁定在中等程度,避免战略误判;若美中对抗加剧,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将更靠前,中日摩擦上升的空间随之扩大。
其次,台湾地区局势具有溢出效应。台海若维持相对稳定,中日紧张度可控;若局势波动,日本的风险感知将随之攀升,使双边互动更敏感。
此外,区域国家的战略选择也会影响中日关系。韩国、东盟若在经济与安全上保持“两线多向”,将为中国与日本之间提供缓冲;反之,则可能加深地区集团化格局。
五、可能的“收场方式”:一种长期的平衡,而非终曲
综合结构、行为与外部变量,中日关系的“收场”更像是一种趋势,而非结果:
第一阶段:紧张持续但可控(未来1—3年)。安全摩擦反复出现,但在最低限度对话框架内被管理。经济关系保持局部合作,政治互信受限。
第二阶段:竞争固化,开始制度化管理(3—7年)。双方或将建立更正式的危机沟通机制,在安全议题上形成“底线共识”;经济上形成稳定的“分区式合作”。
第三阶段:稳定与竞争并存的长期格局(7年以上)。若区域结构出现新的平衡,中日可能重新回到“冷和平”;若地区对立加深,则维持在高风险均衡状态。
无论哪一种,中日关系都不会迎来明确的“结局”,而是在长期竞争中寻找稳定,也在结构性摩擦中维持可控。
结语
中日关系的未来,不是走向破裂,也不指向某种理想化和解,而是进入一种新的常态:竞争长期化、摩擦可管理、合作分领域化、风险外溢带有周期性。所谓的“收场”,更像是一个不断被各方动态调节的区域秩序,而不是某种终止点。在这一区间内,双方需要的不是期待剧烈转折,而是发展能够容纳分歧的机制,并在复杂的东亚格局中寻找新的均衡方式。
毕研韬系《无界传播》总编辑、中国国际传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