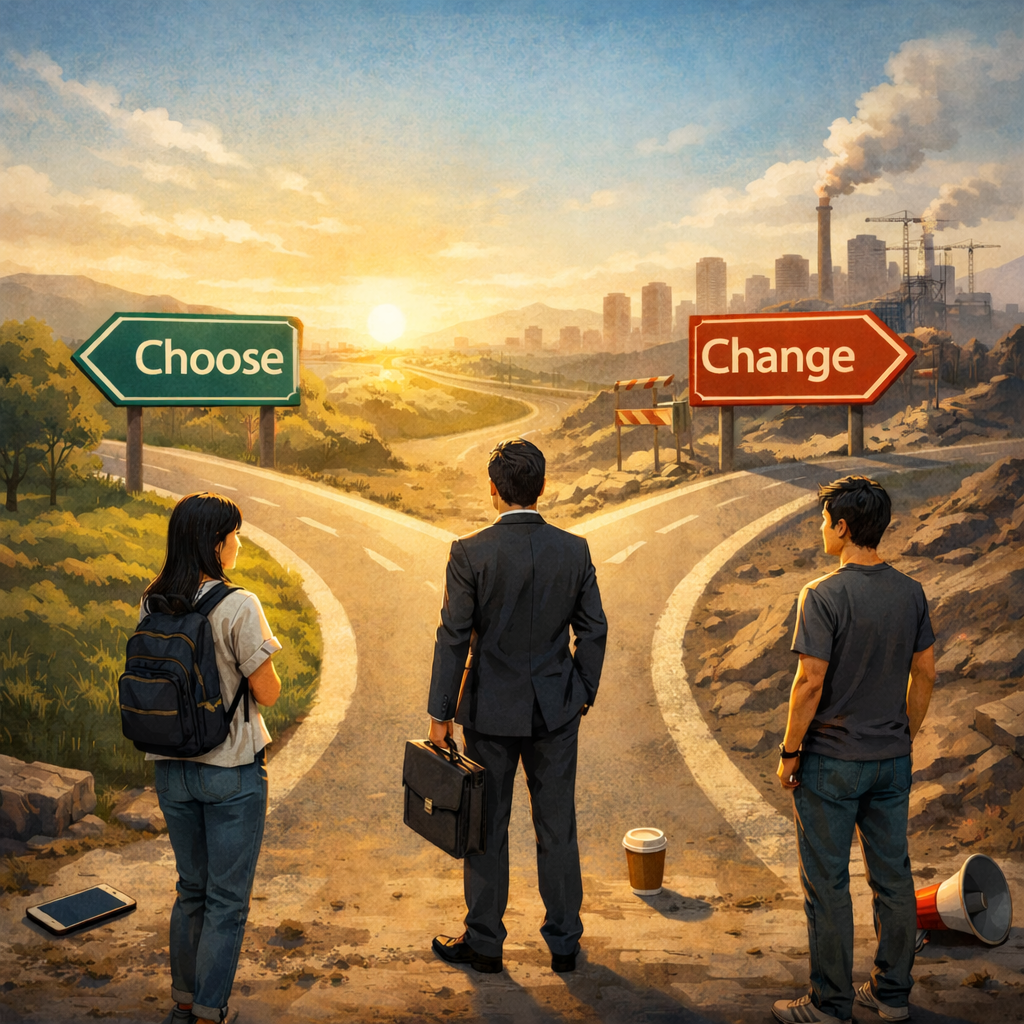“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对穆斯林的情绪化排斥,更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化、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现象。
文/毕研韬
要理解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的成因,需要置于宏观历史结构、中观制度话语、微观心理互动的多层框架中考察,这样才能看到各层如何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这一情绪与观念。
一、宏观层:历史与结构性根源
- 殖民与东方主义的延续效应
西方殖民时代形成的“东方主义”叙事,把穆斯林世界描绘为落后、专制、非理性的他者。这种刻板印象在殖民结束后仍在教育、文学、艺术和学术中延续,构成了伊斯兰恐惧的文化土壤。当现代社会遇到安全事件时,这种历史形象会被迅速激活,成为敌意的“熟悉模版”。 - 地缘政治冲突与安全化逻辑
冷战后,部分西方安全话语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直接绑定。9·11 事件等重大袭击事件,把伊斯兰符号嵌入国家安全叙事,导致穆斯林群体被整体化为潜在威胁。在国家安全框架内,公众很容易接受对穆斯林群体更严格的移民管控与监视措施,这强化了社会的戒备和排斥。 - 跨国移民与社会结构变化
在全球化与人口流动背景下,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北美等地比例增加,加之经济结构调整和就业竞争,引发部分群体的资源焦虑。这种结构性压力常被转化为文化冲突叙事,使穆斯林身份被视作社会变动的“替罪羊”。
二、中观层:制度与话语的放大机制
- 媒体生态与危机化叙事
大众媒体和社交平台在报道涉及穆斯林的事件时,倾向于放大暴力与极端案例,弱化日常生活与积极贡献。这种选择性曝光造成“可得性启发”,使公众高估与伊斯兰相关的暴力风险,从而在感知层面持续制造恐惧。 - 政治动员与民粹策略
一些政党利用“伊斯兰威胁”作为动员议题,将其包装成“保护本国文化与安全”的诉求,以争取选票。这种策略不仅在法律与政策上形成对穆斯林的不利安排,也在公共舆论场中固化了伊斯兰恐惧的政治正当性。 - 法律与治理中的制度化偏见
反恐法律、移民制度、着装规定等政策往往在执行中对穆斯林群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这种制度化不平等,会使穆斯林身份在社会中被“标记化”,进一步加深主流社会对其特殊性与可疑性的认知。
三、微观层:心理与社会互动机制
- 认知偏差与情绪逻辑
人们在面对陌生群体时容易依赖刻板印象做快速判断。当这些刻板印象与恐惧、愤怒等情绪相连时,就形成稳定的情绪化偏见,即便事实信息出现,也难以修正。这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恐惧”在缺乏直接接触的社区中反而更强烈。 - 宗教文本的多义与极端化解读
穆斯林内部少数激进派对《古兰经》及圣训的选择性解读,并通过暴力行为扩大其政治影响,使外界将这种极端化理解误认为是伊斯兰教义本身,从而将个体行为归因于整个宗教传统。 - 跨国连结与事件外溢
全球化下的媒体和社交网络,使某地的极端事件迅速传遍世界,进而影响对远方穆斯林社区的看法。这种“事件外溢”效应,使得即便在本地没有冲突,也可能出现高度的伊斯兰恐惧情绪。 - 种族化与交叉压迫
穆斯林身份常与肤色、族裔、穿着等外显特征绑定,形成种族化过程。这种视觉化的身份识别,使得穆斯林在公共空间中容易成为监视与歧视的目标。 - 教育与知识生产不足
主流教育体系对伊斯兰历史、文化的呈现常停留在片段化、冲突化的内容,缺乏细致和正面的叙述空间。这种知识真空为刻板印象和恐惧的持续提供了土壤。
三、结语
“伊斯兰恐惧”并非单一原因驱动的情绪,而是历史遗产、制度机制与心理认知多层次因素作用的结果。宏观层的结构性条件为它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基础,中观层的制度与话语机制不断放大并固化这种情绪,微观层的心理与互动模式则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它。三者的联动,使“伊斯兰恐惧”不仅顽固存在,而且具有跨国流动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作者系传播学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