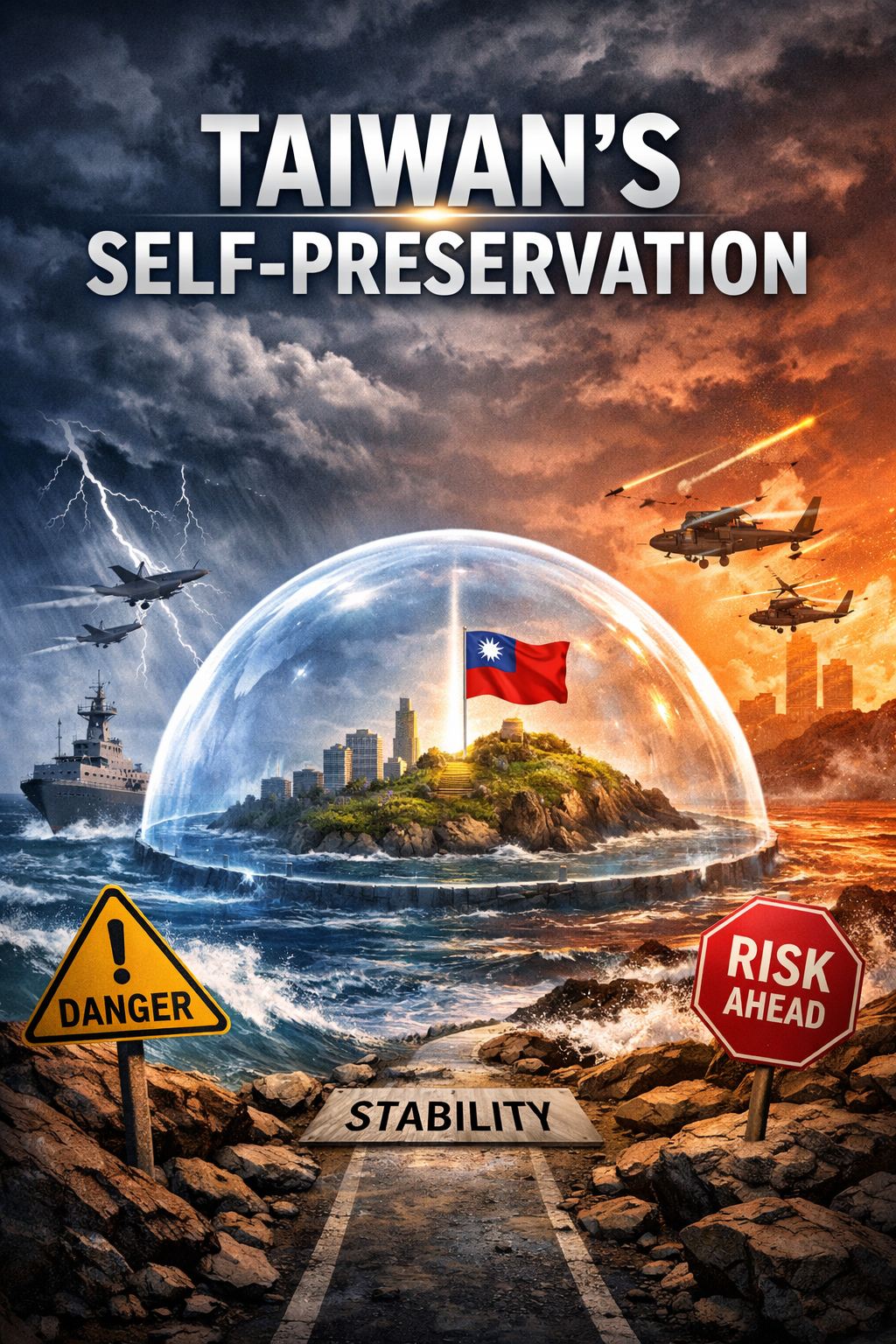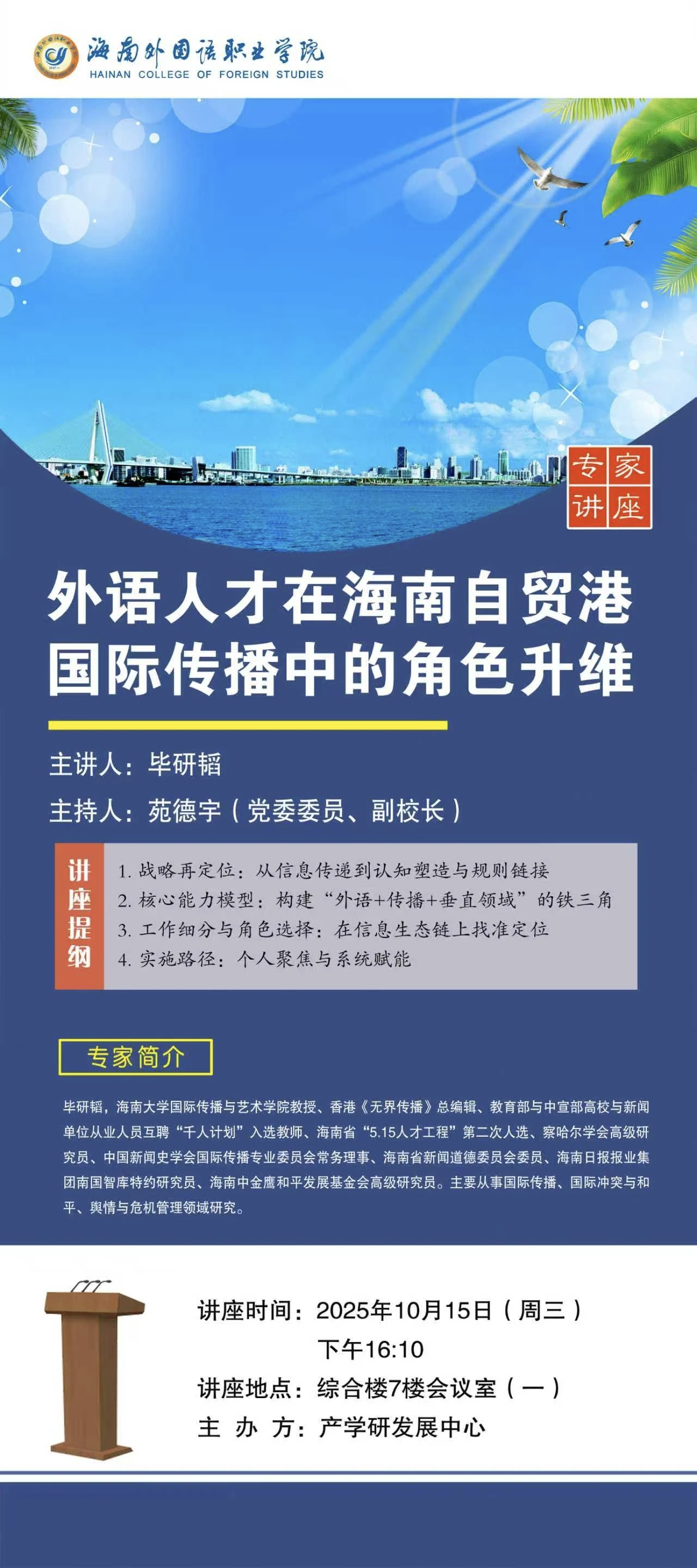台海战争
当下的台湾应如何自保?——从风险控制视角看台海局势
在台海语境下,“自保”意味着把风险管理置于情绪动员之上,把避免最坏结果作为最低共识。 文/毕研韬 在高度情绪化、对立化的舆论环境中,“自保”这个词往往被误读为对抗、动员,甚至战争准备,但如果回到更冷静的现实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台湾真正需要防范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被结构性地推向“不得不开战”的位置。 一、自保的前提:认清“决定性变量”不在军事层面 在台海问题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首要变量。更具决定性的,是三点: 这意味着一个不太直观却至关重要的判断:一旦被认定为触碰政治红线,任何军事“吓阻”都会迅速失效。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自保,就不再是“防守能力是否足够”,而是是否还保有刹车能力。 二、政府层面:自保不是表态管理,而是红线管理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台湾当局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持续抬高立场,而在于精确管理红线感知。 1.避免“不可逆”的政治动作 象征性表态可以反复修辞,但制度性、法理性、结构性的改变一旦发生,往往难以回撤。真正的自保,是在任何政策选择中都反复自问:这一动作是否会被解读为质变,而非量变? 2.把“战略模糊”视为安全资产 战略模糊不是软弱,而是一种风险缓冲机制。它为各方保留了解释空间,也为时间争取了价值。一旦把未来锁定在单一终局叙事中,短期的政治满足感往往会换来长期的安全脆弱性。 3.降低象征性对抗,强化实务性互动 高调的政治站位,可能带来短期舆论收益,却会压缩危机管理的空间。相反,低调、技术性、功能性的对外合作,更有助于在紧张结构中维持稳定。 三、社会层面:自保首先是“认知自保” 一个社会如果在心理层面提前进入战争状态,现实中的风险反而会急剧上升。 1.警惕战争叙事的日常化 当战争被频繁地当作道德命题、身份试金石来讨论时,社会对复杂性的容忍度会迅速下降。不同意见被视为“不忠诚”,而不是风险提醒,这正是误判最容易发生的土壤。 2.拒绝“英雄化冲突”的想象 历史反复证明,战争最容易在被浪漫化时发生。当牺牲被提前合理化,理性计算就会被边缘化。真正负责任的公共讨论,应当把生命、生活与代际延续置于抽象价值之前。 3.区分身份认同与生存策略...
2026-01-01美国发布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台湾成关键变量
文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2025年版《中国军力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报告中“台湾”一词被提及232次,显著高于以往版本,显示台湾议题已被系统性纳入美国对华军事与安全评估的核心分析框架。 报告显示,台湾不再仅作为单一地区热点被讨论,而是被置于中国军事能力建设、作战情景规划、威慑态势评估以及印太安全架构等多重分析之中,成为美方衡量对华战略风险的重要变量。相关内容贯穿多个章节,涉及陆、海、空、火箭军以及信息与联合行动能力等领域。 报告还多次以2027年作为能力评估节点,指出中国正推进相关军事现代化目标,并假设届时解放军在台海方向可能具备更成熟的作战能力。美方在报告中强调,该时间点主要用于防务规划与情景推演,服务于风险评估和力量建设,并不构成对具体政治决策或行动时间的判断。 分析人士指出,台湾在报告中的高频出现,正在产生多重持续影响:一是进一步强化美国国防规划中以台海为核心的情景设定,影响相关兵力部署与资源配置;二是向盟友与伙伴传递战略重心信号,推动地区安全讨论持续围绕台海展开;三是通过高频叙事塑造国际舆论环境,使台湾议题在中美关系与区域安全议程中的权重不断上升。
2025-12-25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文 / 唐摩崖 台海局势正悄然进入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临界点。当“和平统一”不断被岛内政治现实蚕食,“不排除使用武力”成为大陆对外最清晰的信号时,一个不愿想象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在逼近决策与认知的核心: 台海一旦开战,结局将如何? 这不只是军事推演的问题,更是关于战略目标、国家意志、全球博弈和民族心理的多重叠加。本文尝试分析三种可能的战争结局,并对其实现概率做出初步评估。 结局一:全面统一,概率为65% 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结果。大陆已在军事、制度与心理层面完成准备,若决定开战,不会容忍“打而不统”或“中途止损”的结局。 大陆如选择动武,其目标不会是“惩戒台湾”或“局部控制”,而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达此目标,冲突即失其意义。 全面统一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三方面:解放军迅速夺取制空制海权;“斩首行动”彻底摧毁台湾指挥体系;外部干预未能形成有效阻断。 必要时,北京可能不惜将台军主要抵抗力量与政府建筑彻底摧毁,以压缩战后整合成本。 统一后的政治治理、秩序恢复、岛内民意转化将是另一场“非军事战争”。大陆或将设立临时军政管制机制,随后推进行政重构与国家意识形态整合。 结局之二:局部占领+准统一,概率为25% 一种非预设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大陆夺取部分关键地区(如西岸城市、政经中枢)或全岛控制尚未完成,但台湾政权体系已崩溃,岛内进入政治真空状态。 具言之,这会出现如下情况:岛内存在局部抵抗,军管区与民控区并存;名义上已“统一”,但国家治理版图尚不完整;台独势力在岛外建立“流亡政府”;国际社会不承认统一合法性,但制裁力有限。 这种状态下,大陆可能宣布统一已完成,此后进入长期整合期。 此结果源自战争节奏控制不理想,或因外部干预、岛内游击式抵抗导致“战而不稳”。虽然政治上不理想,但比失败更可接受。 结局之三:武攻失败或被迫中止,概率不足10% 必须承认一种极端情境:大陆发动战争但未能达成战略目标,或被国际军事力量有效阻断,被迫中止行动。 这种情况将导致政治合法性受损;外部制裁全面升级;台海形成新对峙格局。 这种结局的实现条件包括美日联军直接介入或“准参战”;解放军补给线被切断,长期无法推进;国内发生重大经济金融震荡,无法支撑战事。 这类结局与大陆当前的战略部署严重不符。除非误判外部干预强度或遭遇严重战场意外,否则北京极难接受“战而不成”的后果。 为什么“战而不统”基本不可能?...
2025-05-22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美国人精于博弈。他们善于模糊承诺、制造不确定,以此最大化战略空间。 于是他们相信:中国口中的“红线”不过是谈判筹码,而非真正底线。 他们以为,北京所说的“台独即战争”,不过是为了威慑台湾和美国,而非真的准备一战。 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在中国文化中,“红线”不是谈判语言,而是政治誓言。如果触线而不动手,北京将担不起历史骂名,更无法向社会交代。 对中国来说,统一不是选项,而是使命;“武统”不是首选,但一旦必须,就绝不退让。 误判三:把“中国的理性”误解为“我们的理性” 这是最深的误解,也最具有结构性。 美国长期自信于自己“理性至上”的战略文化,相信其它国家都会像他们一样,在权力、成本、收益之间做出“合理”选择。 所以他们反复告诉自己:中国不会冒着毁掉经济、被全球制裁的代价以武力收复台湾。 但他们没能意识到:这是美国文化中的“合理”,而不是中国文化中的理性。 中国的理性是整体性的,不是短期博弈的;是历史性的,不是财报导向的;是文明性的,不是竞选驱动的。...
2025-05-18文章推介
“一带一路”:国际社会怎么看
【编者按】本文由ChatGPT生成,文中所列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动机,是ChatGPT想定的外部猜测。编辑修改了文中个别语句,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使之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以下是ChatGPT的分析) 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迅速成为中国推动全球合作与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作为一项宏大的国际合作计划,“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增进文化交流,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对这一倡议的看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度。由于经济、地缘政治、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这一倡议的评价不尽相同。 一、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动机 中国的主要动机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经济增长与区域合作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增长,特别是支持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机遇,同时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复苏和繁荣。通过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和贸易合作,中国期望与世界各国实现共赢。 (二)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稳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尤其是中亚和中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通过投资建设跨国油气管道和运输通道,可以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从而提升国家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保障能源供应和稳定的物流链条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三)战略影响力与外交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客观上也是中国提升全球战略影响力的工具。通过提供融资和基础设施支持,中国在沿线国家树立了积极的形象,增强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从而扩大了在亚非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的这种外交战略不仅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也为中国争取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四)推动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
2025-02-16毕研韬教授赴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外语人才如何赋能自贸港建设?毕研韬教授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交流。 文/唐摩崖 2025年10月15日下午,应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黄学彬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赴该校开展学术交流,并作题为《外语人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角色》的专题报告。报告由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苑德宇教授主持,相关专业50余名教师参加了交流活动。产学研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博作总结发言。 在报告中,毕研韬教授指出,外语人才应从“翻译者”向“认知塑造者”转型,这一过程需要系统学习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意义建构与传播效果相关知识,并注重传播生态的整体建构。毕教授还重点分析了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传播生态,结合实践探讨了外语人才的转型路径与能力要求。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始建于1947年,是海南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坐落于中国首个滨海卫星发射基地——文昌市,目前已开设18个外语语种课程,实现东盟语种全覆盖,是全省外语语种设置最为齐全的高校。
2025-10-16从26国阵容看中国“朋友圈”:抗战纪念的外交地理学
26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名单,体现中国的外交格局和当今世界的合作版图。 文/唐摩崖 8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刚果(布)总统萨苏,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 那么,这个名单里隐藏着哪些外交密码? 一、总体特征 1.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盘是稳固的。 2.多边框架是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参与或发起的多边机制,是其汇聚合作伙伴、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3.“一带一路”是重要纽带:这26个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度重合,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更成为中国与参与国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纽带。 4.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战略上的分歧,使得高层交往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恢复。 5.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协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位列榜首,备受国际关注。国际观察者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互动。 6. 全部属于“全球南方”:...
2025-08-28《无界传播》:透视中国的新窗口
文/毕研韬 2025年3月7月,《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 2024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引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厘清中国高层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非常重要”。 2020年7月,美国某著名大学有项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结论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不可思议的是,几年之后美国才有专家对此进行反省。 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等因素交叠震荡,令外界很难了解当今中国。 前些年,我还偶尔关注下海外华人关于中国的评论,现在早已懒得看了。出去若干年后,他们一方面深受海外影响,另一方面已不了解今日中国了,导致对中国的解读常常黄腔走板。 如今,《无界传播》将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新窗户,有助于外部触摸当今中国真实的脉搏。 与此同时,《无界传播》也是国人了解国家的一个渠道。 中国高层基本依赖内参系统了解环境,而普通百姓主要通过大众传播了解世界,但今天这两个系统都已功能失调,不堪重负了。此时此刻,《无界传播》迎难而上,引领用户在重重迷雾中发现中国、认识世界。 这是《无界传播》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使命。
2025-03-25中美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共同点与分歧点
文/唐摩崖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言行一直引发关注。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两国对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既有部分交集,也存在深层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价值理念与全球角色定位,更折射出当前世界秩序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 一、表层立场的交集:避免失控,强调稳定 尽管中美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态不同,但在某些宏观原则上,两国存在一定共识。 共同强调主权原则。美国以“捍卫乌克兰主权”为基本立场,强调国际秩序不可因武力改变国界。中国虽然拒绝谴责俄罗斯,却同样在多个场合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此作为政治解决冲突的前提。 反对战争升级尤其是核风险。两国均明确反对在乌克兰战场上动用核武器。中国多次重申“核战争打不得”,美国也一再警告俄罗斯不得动用核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美在维护战略稳定方面的底线共识。 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尽管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中国则与俄罗斯保持高层互动并加强经贸联系,但双方均未跨越军事介入的红线。这反映出双方都试图控制战争外溢,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漩涡。 二、核心分歧:战争性质与责任认知不同 中美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战争性质的认定、责任归属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角色的理解上。 对战争的定性南辕北辙。美国将俄乌战争视为侵略行为,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借此塑造“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则更强调冲突的地缘背景与历史根源,认为北约东扩不可忽视,主张“劝和促谈”而非对抗升级。 对俄罗斯的角色定位截然不同。在美国战略认知中,俄罗斯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破坏者,是应被孤立和削弱的对象。中国则将俄罗斯视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伙伴。这种差异导致中方即使不支持战争本身,也始终保持对俄关系的政治稳定性。 在全球舆论场的博弈方式不同。美国主导西方叙事体系,通过媒体、联盟体系强化对俄罗斯的道义谴责,同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化”处理,指责中国“间接援助俄罗斯”。中国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塑造“中立调解者”形象,强调自身并未提供武器援助,反而努力推动政治解决。...
2025-08-05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2025-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