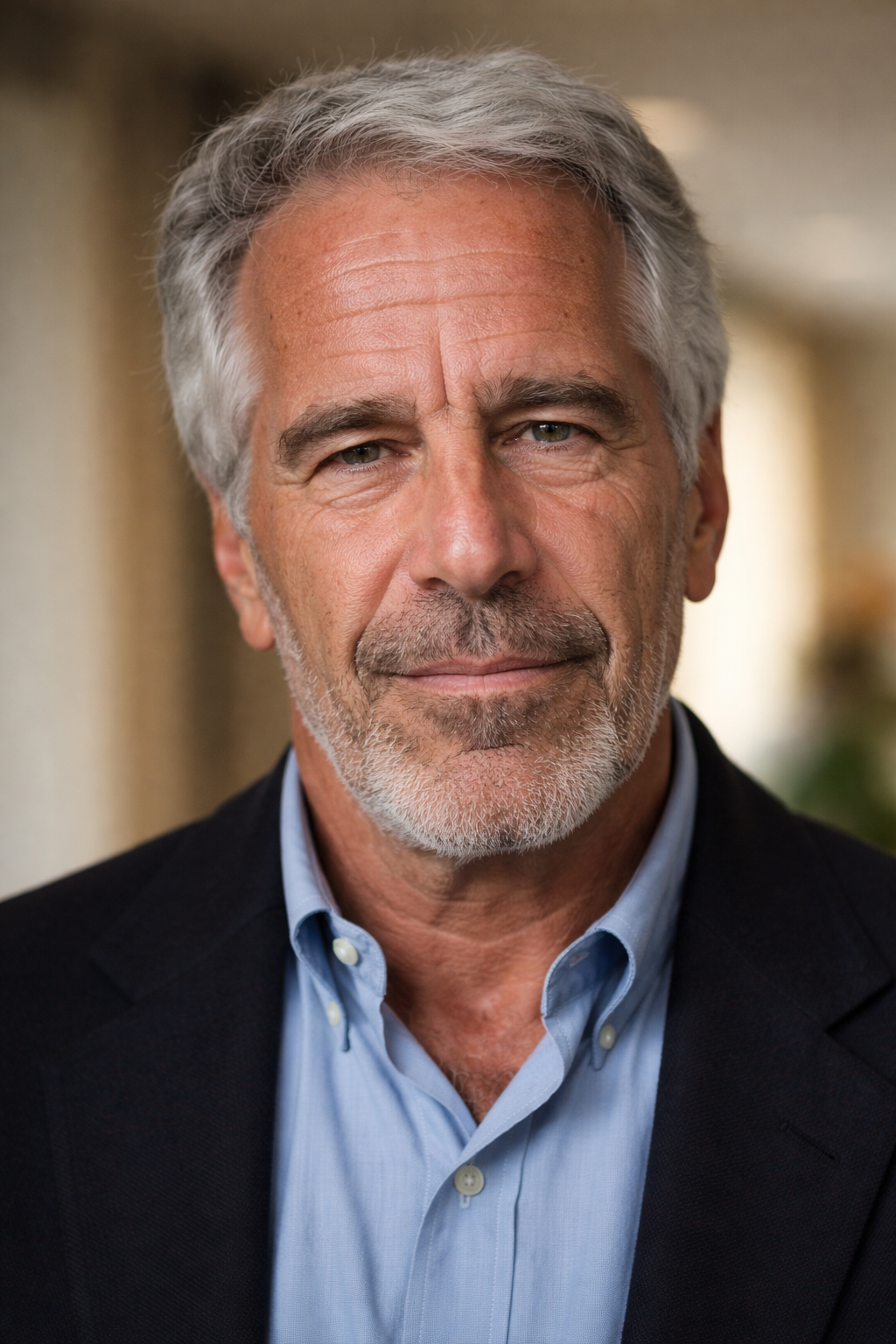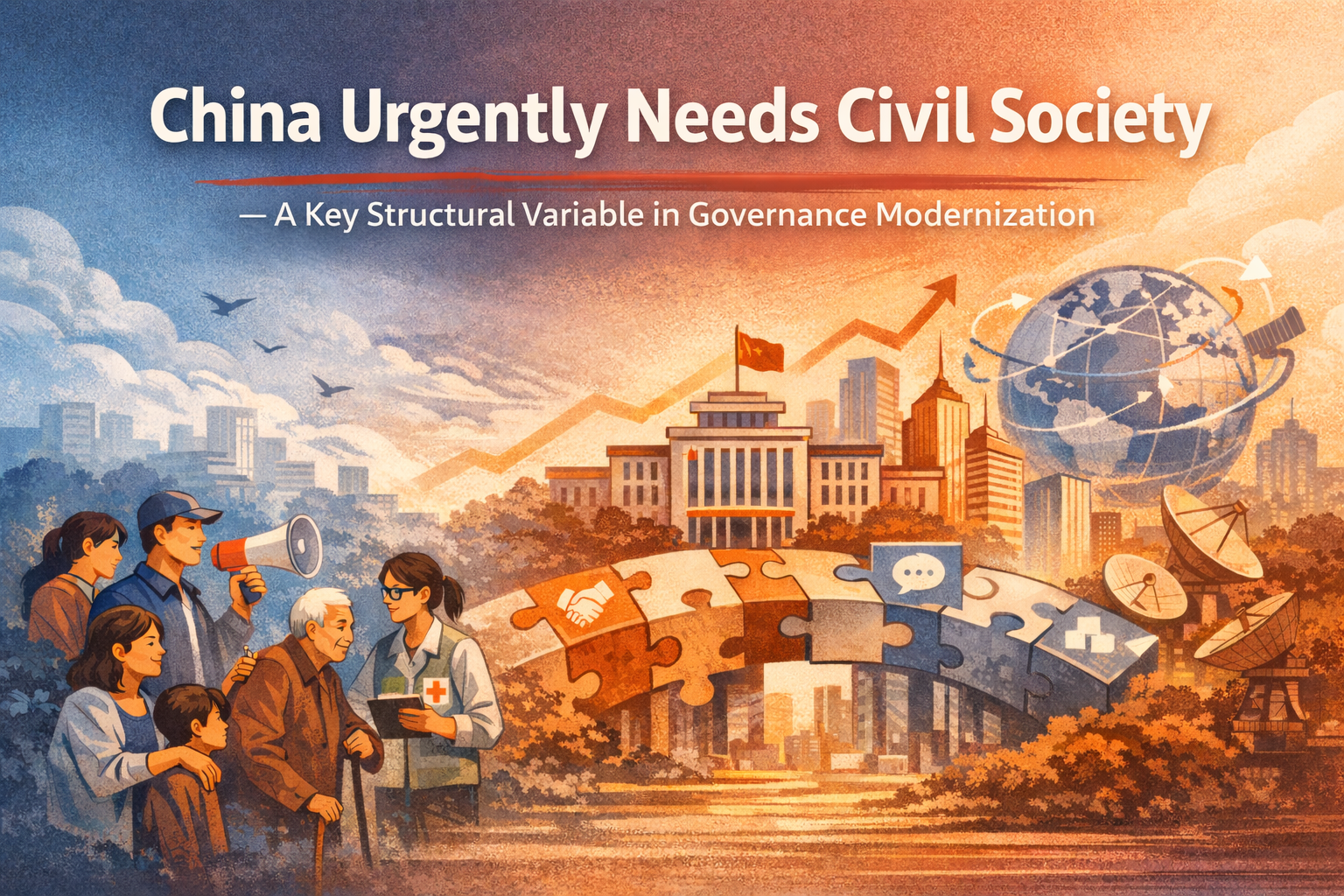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美国人精于博弈。他们善于模糊承诺、制造不确定,以此最大化战略空间。
于是他们相信:中国口中的“红线”不过是谈判筹码,而非真正底线。
他们以为,北京所说的“台独即战争”,不过是为了威慑台湾和美国,而非真的准备一战。
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在中国文化中,“红线”不是谈判语言,而是政治誓言。如果触线而不动手,北京将担不起历史骂名,更无法向社会交代。
对中国来说,统一不是选项,而是使命;“武统”不是首选,但一旦必须,就绝不退让。
误判三:把“中国的理性”误解为“我们的理性”
这是最深的误解,也最具有结构性。
美国长期自信于自己“理性至上”的战略文化,相信其它国家都会像他们一样,在权力、成本、收益之间做出“合理”选择。
所以他们反复告诉自己:中国不会冒着毁掉经济、被全球制裁的代价以武力收复台湾。
但他们没能意识到:这是美国文化中的“合理”,而不是中国文化中的理性。
中国的理性是整体性的,不是短期博弈的;是历史性的,不是财报导向的;是文明性的,不是竞选驱动的。
为了统一,中国可以忍耐几十年;为了统一,中国可以牺牲数代人的现实利益。这是一种理性,但美国理解不了。
真正的风险是认知不对称,而不是实力不对称
今天,台海最大的风险不是某一天北京突然动手,而是中美对彼此的误解已接近临界点。
北京的底线思维和历史责任感,被美国误解为民族主义冒险,而华盛顿的“战略模糊”和双边操作,被北京视为试探统一红线。
一方在下最后通牒,而另一方却以为“这只是恫吓”,这时战争就不再是概率问题,而是误判的必然结果。
结语:当误解变成结构性的镜像
真正危险的不是台独分裂势力,而是华盛顿总是在镜像北京:用自己的逻辑,想象中国的行为。
他们误把台海危机当作博弈筹码,却没意识到对北京而言,这绝不是筹码,而是一个关于民族、历史与政权合法性的三重底线。
他们总是用“美国那套”理解中国,却忘了中国不是美国。
而我和《无界传播》要做的,就是将这种认知错位揭示出来,让世界明白:如果看不清中国与自身的的认知结构,你就永远不懂中国的行为逻辑。
作者系中国大陆传播学教授、国际传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