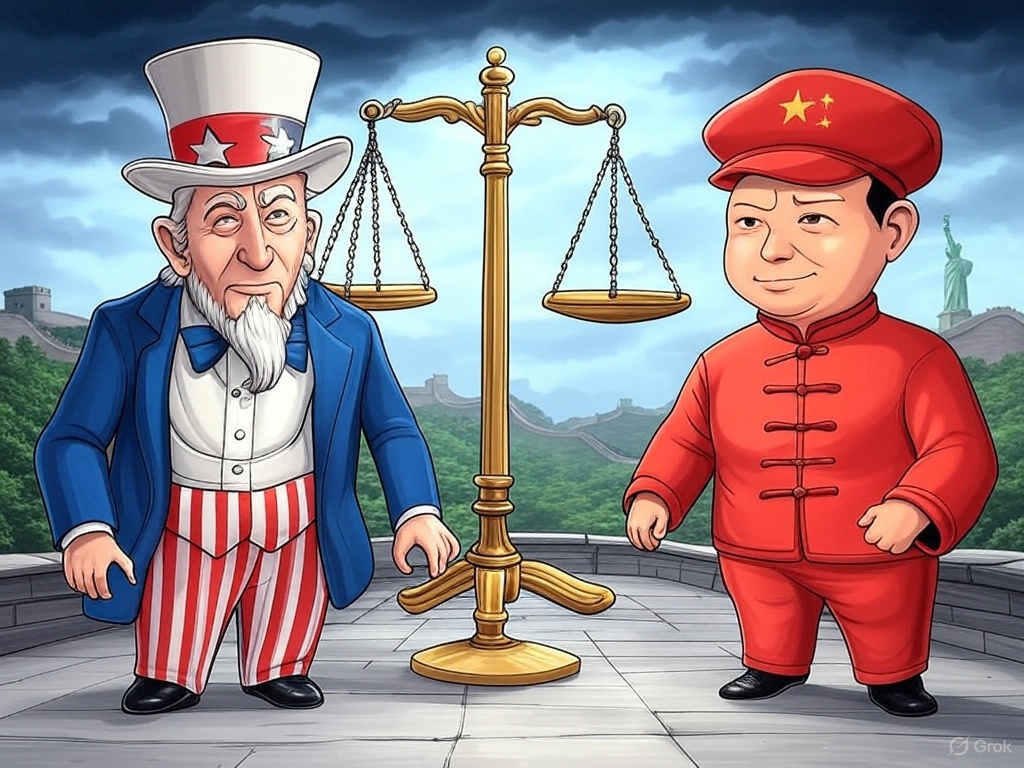中美科技竞争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2025-10-25文章推介
澳洲前驻华大使:“霸权替代论”解释不了中国
文/毕研韬 在当下西方对华讨论中,“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判断、推论与政策设计,构成了大量战略报告、媒体评论与公共讨论的认知底座。然而,澳洲前驻华大使 Geoff Raby 在其新著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2026-01-17海南自贸港:中美贸易战的“缓冲区”
——《南华早报》对海南自贸港的最新解读 文/毕研韬 2025年7月23日,北京正式宣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2025年12月18日封关运作,国际社会迅速聚焦这一制度实验的地缘意义与全球影响。《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中国开放格局下的一个前沿阵地,更可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扮演“缓冲区”(buffer zone)的重要角色。 在中美博弈中寻求“空间弹性” 报道引用政策研究人员的观点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关税壁垒加剧、技术脱钩趋势未减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有潜力充当中美贸易之间的“中性平台”或“制度过渡带”。其高度开放的税收制度、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和“境内关外”的政策安排,使其既能嵌入中国国内消费循环,又有望对接国际市场规范,成为中美经济之间“仍可合作”的灰色地带。 这种“缓冲”并非指政策妥协,而是通过灵活、弹性的制度配置,为中外企业提供一个避开高关税、试水合作路径的“制度缓冲池”。例如,外资企业可在海南设立基地,在规避关税的前提下向中国内地和亚太市场供货,而中国企业也能通过海南参与国际竞争,试探新型全球市场机制。 推动制度对接与供应链重构 《南华早报》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也可能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去中国化”趋势下的重要制度回应。通过建立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和贸易机制,海南可吸引那些不愿完全脱钩、但也不愿完全依附中美任何一方的全球企业,从而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提供一个“中间选项”。...
2025-07-24Prof. Bi Yantao Congrats the Opening of the Asia Art Museum in Haikou
Congratulations on the Opening of the Asia Art Museum and Its Inaugural Exhibition...
2025-12-17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2026-01-21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2026-01-03中美关税大战:不会终结,只会分化
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202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