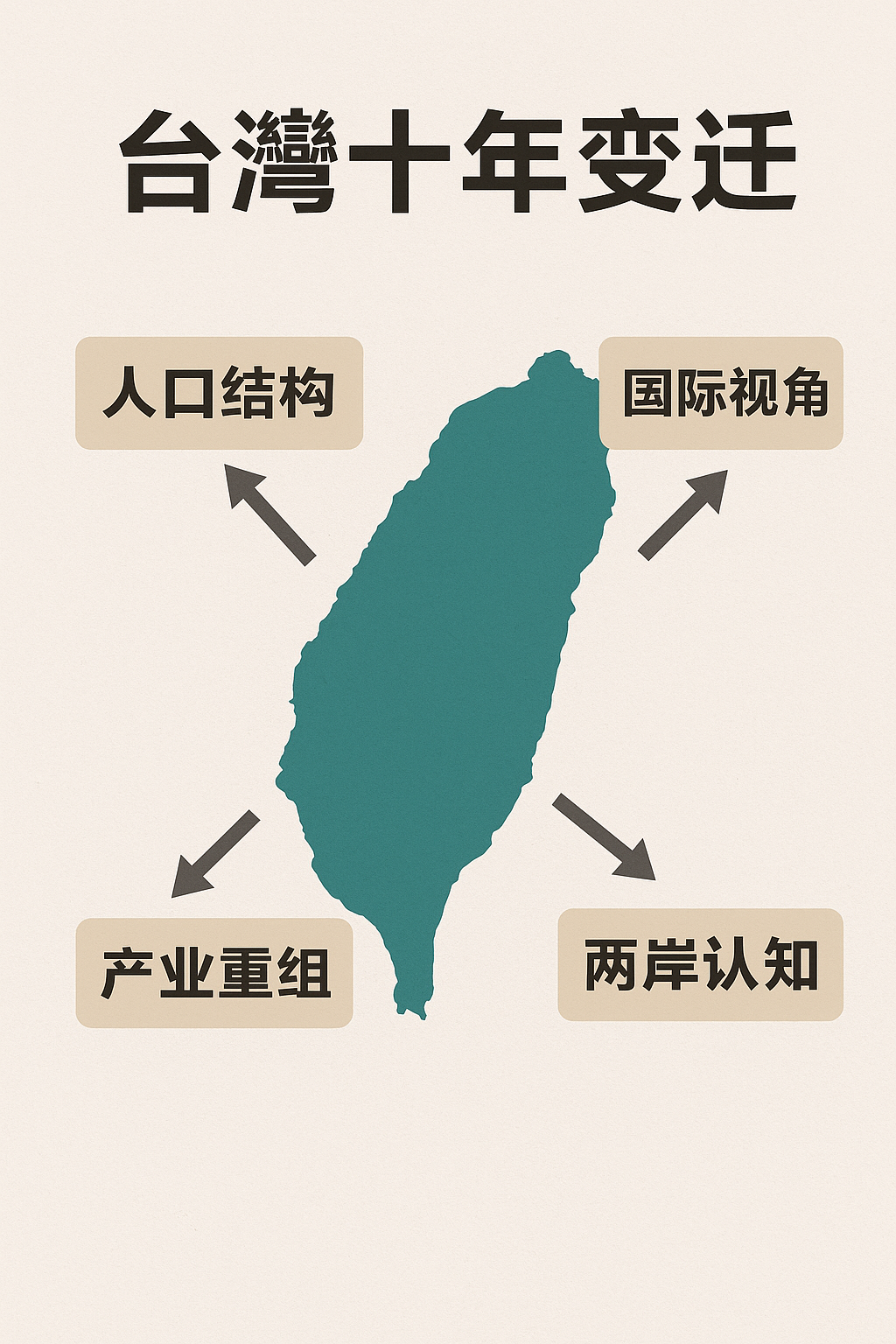上层社会
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2026-01-03文章推介
一线教师“保命法则”
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2025-06-30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2025-08-03香港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转型
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2026-02-26从乌克兰到以色列:战争为何越来越相似?
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2025-07-15过去十年,台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过去十年,台湾的人口、产业、国际观、两岸认知都在同时转向,一个全新的台湾已经浮现。 一、人口断层与老龄化挑战 根据台湾当局统计,截至 2025 年 10 月,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 19.9%,逼近“超高龄社会”门槛。 与此同时,台湾总人口已连续多年自然负增长,新生儿数持续下滑。...
2025-11-21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2026-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