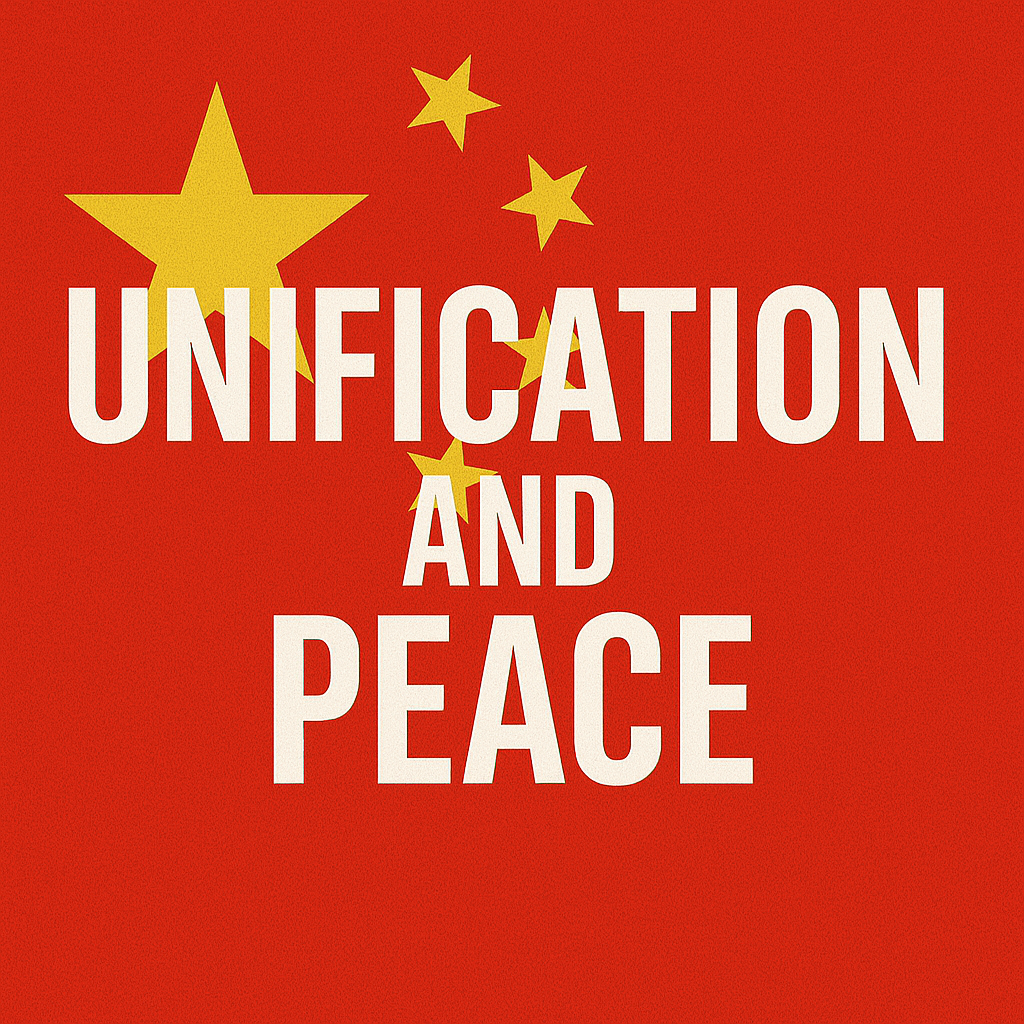文/毕研韬
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中美关税谈判成果时说:
“他们(中国)已经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极好的,对我们(美国)来说也将是极好的,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统一与和平。”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us,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for unification and peace.)
这个表态立即引起了台湾和国际观察者的关注。“unification and peace”(统一与和平)这一词组出现在中美贸易语境中极不寻常,它极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大陆处理台湾问题时惯用的政治语言:“和平统一”。
美国澄清:只是贸易,不涉台湾
面对外界猜测,美国在台协会(AIT)于次日(5月13日)澄清:特朗普总统提及的unification并非涉台表态,而是指中美之间在经济制度上的协调与互通。白宫方面未对该表述作进一步解释,也没有修正或补充总统的原话。
我的解读:这不是语误,而是战略模糊
我认为,这句话引发的联想并非空穴来风。从传播学视角和特朗普本人的语言风格来看,这更像是一种有预谋的战略模糊表达,而非简单的即兴口误。
首先,unification是高政治敏感词。在中美贸易语境下,几乎没有语义需求会让美国总统使用这一表述。即便要表达制度趋同、市场协调,美国政治语言中更常使用integration(整合)、alignment(对齐)等术语。“unification”则常用于国家统一、主权并轨等政治话题,尤其在中文世界,对应的正是“统一台湾”的表述框架。
其次,在中美关税语境下,unification(统一)与peace(和平)并列使用,非同寻常,甚至可以说是极具政治意味的“话语越界”。unification与peace 这类词,往往出现在战争、地缘冲突、国家分裂等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中,极少在经贸表述中被并用。在中美官方语言体系中,unification 的默认联想几乎都指向“两岸统一”;与peace组合出现,更进一步强化了与中国大陆倡导的“和平统一”的对应。
特朗普此举,相当于在一个技术性语境中植入强政治象征,传播学上称为“嵌套异议语境”(contextual re-embedding),也就是把本不属于此语境的话语强行植入,引导受众重构焦点。
其三,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期间,尽管中美之间的关税争端再次升级,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高官在公开场合中并未直接将这场争端称为“战争”(war),所以特朗普使用“和平”(peace)一词显然是有意为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更倾向于使用“经济独立”(economic independence)和“解放日”(Liberation Day)等表达方式。他和政府高官们都倾向于将关税措施描述为实现公平贸易和保护美国利益的手段。
当然,在特朗普第一届任期内,他和政府高官都多次将中美关税争端称为“战争”。譬如,2018年3月2日,特朗普在X平台(原推特)上写道:
“当一个国家(美国)在与几乎所有贸易伙伴的贸易中都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贸易战是好的,且容易赢。”
(When a country (USA) is losing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on trade with virtually every country it does business with, 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
这是特朗普最著名的“贸易战”表态,明确将关税冲突定义为“战争”。
其四,特朗普一贯策略性地使用语义模糊语言。他擅长通过模棱两可的用词释放政治信号,在不承担明确政策责任的前提下,对内赢得支持,对外制造压力。其第一任期内就曾多次用“我们会看看”之类语句模糊台湾、乌克兰等敏感议题的立场。此次“unification and peace”的话术,也可被理解为对中国大陆的一种话语试探——暗示美国可能更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也可能暗藏威慑意味。
其五,从时机来看,这段话出现在中美谈判刚达成妥协之际。特朗普选择在此时将“统一与和平”植入贸易成果发布会上,其话语结构本身就具备“搭载次议题”的可能性。
战略模糊的传播效果:可控误解,试探舆情
特朗普此类语言操作所依赖的,正是传播学中的“战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通过一组容易产生歧义的关键词,制造多重解读空间,令不同受众各取所需。
- 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是对“和平统一”话语的模糊呼应;
- 对台湾而言,这是不安的警号,暗示可能失去美方承诺;
- 对美国国内,则是对保守派的暗示:总统正在“驾驭中国”;
- 对全球舆论,这制造了不确定性,迫使各方进入再阐释状态。
另一种可能:特朗普无意间释放了本真想法
在国际上,一直有部分人认为,如果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趋同,两岸统一的阻力会大幅减少。这一次特朗普是不是在说,如果中国全面开放,市场和制度与美国趋同,对中国来说将是有利的,因为这将有助于实现台湾海峡的统一与和平?我认为这一解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结语:在语言的临界点上感知地缘变动
“Unification and peace”不只是一个词组,而是一种外交语言的临界表达。在全球秩序重构的敏感时期,正是这种表面和平、实则诱导误解的模糊话语,成为塑造认知边界、引导地缘博弈的重要手段。
传播学研究的价值正在于此:不仅捕捉话语表面意义(surface meaning),更能识别其语境裂缝中的真实动机(implied meaning)。在全球战略语言博弈日趋精巧的今天,透视话语,已成为实施国家战略的必要基础。
作者系中国大陆传播学教授、国际传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