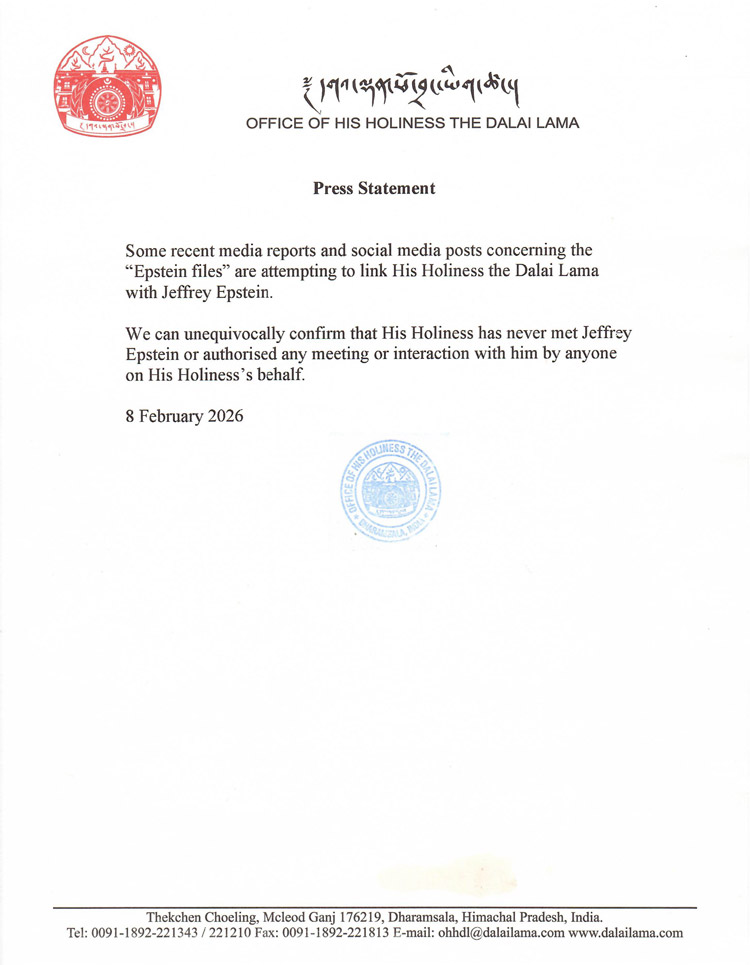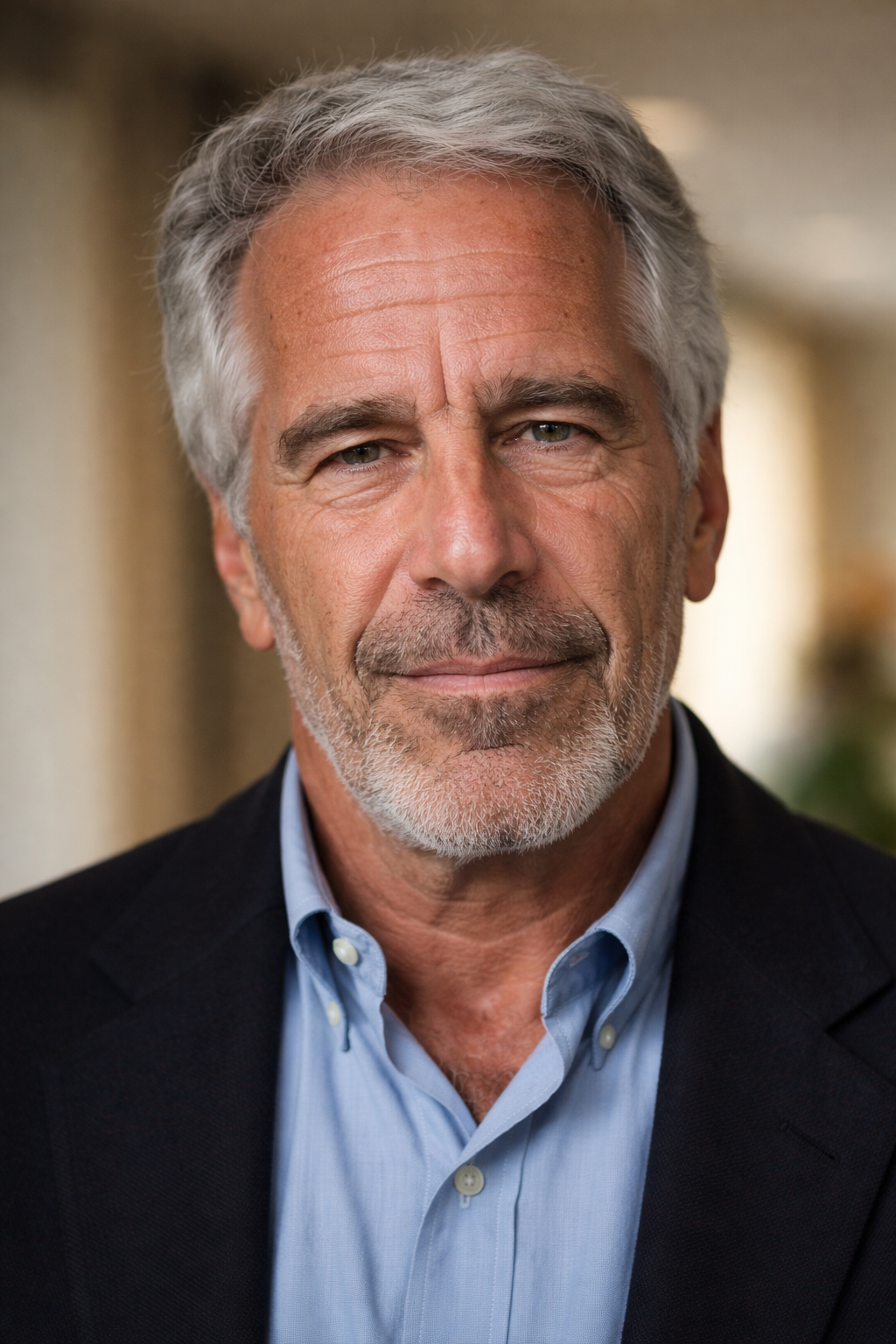中国民间对乌克兰捐款位列全球前列,这说明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并非简单同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乌克兰政府官方募捐平台UNITED24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及媒体整理结果, 2025年度中国在私人(个人)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14位,在机构(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7位。该平台统计覆盖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UNITED24成立于2022年5月,由乌克兰政府主导运作,面向全球个人与法人主体募捐,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支持、基础设施修复、防务及排雷等项目。上述排名仅统计通过该官方平台汇入的捐款金额,不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财政或军事援助,也不涵盖经红十字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渠道的资金。
从统计位置看,在约140个来源国中,中国的私人捐款和机构捐款都已属于明显的“前列水平”,而非边缘或象征性参与。
这一现象至少体现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对俄乌冲突并非单一态度结构。尽管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强调政治解决与战略平衡,但在具体人道与项目捐助层面,中国部分个人和机构却都有亮眼的表现,说明其规模具有统计意义,而非个别行为。
第二,这类捐助具有主体分层特征。私人捐款排名低于机构捐款,可能说明企业或组织层面的资金动员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企业国际业务关联度、跨境责任意识以及品牌风险管理等因素有关。
第三,从国际传播层面看,这一排名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拒绝参与”的外部刻板印象。排序位居全球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参与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该排名仅限UNITED24单一平台,不等同于全球对乌援助总量格局。在国际援助整体结构中,政府间援助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平台统计范围内。
还需要注意的是,该统计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维度的参与情况,并不构成政策信号,但揭示了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差异。